泾川的纵深
到庆阳站下车,旋即又登上去泾川的车子,只觉空气清冽,皮肤有一种干爽之感。而脑海中飞旋的,却是李商隐的“八骏日行三万里,穆王何事不重来?”他的这一句诗歌,与我初来泾川的感觉高度一致,神话是人类文明之初,蒙昧且绮丽,夸张又美好。尽管会觉得怪异和离奇,但天地之间本就藏匿了诸多的秘密。泾川与陕西接壤,其地貌和气候,与秦川蜀地颇多相似。我隐隐觉得,天水、平凉乃至陇南一带,当是中国文明生源之地,也甚至无端以为,西北之地那庞大深厚的黄土,以及莽苍与细腻的颜色,就是决定中华民族基因与肤色的根本所在。而泾川的西王母与穆天子的传说,也似乎能从另一方面佐证我的这一猜测。
公元837年,李商隐受同榜进士韩瞻邀请到泾川,这个韩瞻,确确是李商隐知音,不仅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,且和他做了挑担,即两人同为王茂元女婿。这等艳遇与际遇,在很多时候,是令人羡慕的。李商隐少小家贫,由河南沁阳迁徙至荥阳,蒙令狐楚器重,《旧唐书·李商隐传》说,“商隐幼能为文。令狐楚镇河阳,以所业文干之,年才及弱冠。楚以其少俊,深礼之,令与诸子游。”而令狐楚为“牛党”,即在政治上跟随牛僧孺和李宗闵。而极其欣赏李商隐才华的王茂元,则跟随“李党”,即李德裕、郑覃。
人生福兮祸兮,不过转瞬之间。“牛李党争”环境下,令狐楚、王茂元等人也都是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,但天下人事,向来无常。难得的是,王茂元爱才而不计嫌,不仅把自己女儿嫁给了李商隐,还表奏李商隐为其掌书记。后人如我者,读到这里,只觉得王茂元爱才之德令人钦佩。这个人的一生也算坎坷,唐德宗时期入仕。文宗年间,历任检校工部尚书、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,后攀上权倾一时的郑注,转任泾原节度使,善终。
李商隐之于泾川,得益于生前也颇为显赫的韩瞻,韩瞻是陕西樊川人,也得益于其岳父王茂元,因而一路升迁,先后任虞部郎中,鲁州、凤州(陕西凤翔)、睦州(浙江建德)刺史,他还有一个有名的儿子韩偓,也是一位诗人,只不过,其诗之中,有太多的晚唐之气与凋零之态,韩偓最好的一句诗,我觉得应当是“窗里日光飞野马,案头筠管长蒲卢。”(《安贫》)可以想见,文人及其作品,始终和他们所在的时代有着深刻而密集的联系,诗文和一个历史年代,总有着某种彼此“照应”与“感同身受”“相互成就”的关系。
及至泾川,夜色之中,春意浓郁,不大的城市,华灯流彩,到处都是明亮的烟火。和几个朋友同去宵夜,其中的作家李新立是由平凉赶来的。平凉之地,因六盘山、崆峒山,及至广成子、黄帝问道、汉武帝北巡之神话往事和历史记载,历来为多个王朝的北部屏障,“外阻河朔,内当陇口,襟带秦凉,拥卫畿辅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》)李白《塞下曲》,“兵气天下合,鼓声陇底闻,横行负勇气,一战净妖氛”。1935年10月7日,中央红军顺利翻过这一座古山,毛泽东作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一词,“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,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,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”
杯盏之间,客套之外,便是谈论泾川之地,我以为外来者口气,说起李商隐诗中的“八骏”“穆王”等,所谓“八骏”,即《穆天子传》中所说的“天子之骏”,分别为赤骥、盗骊、白义、踰轮、山子、渠黄、华骝、绿耳。穆天子即西周第五任君主姬满。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战国墓葬的《穆天子传》一书中看,这个姬满生前最喜欢旅行,且无所不至,无所不往,结交的人也都是上古神仙或者地方首领,他的帝王生活是浪漫的,也是探险的,是神话的,也是关于华夏早期地理疆域的。倘若《穆天子传》所载之事确凿,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,古代中国肯定四通八达,西周、东周的地理疆域,也不仅是“古中国”,即陕西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一带,一定延缓得更大更广,而后来所谓的西域及岭南、南诏等地,也是周天子之天下。
历史总是吊诡,充满各种神趣与玄异色彩,或令后人想慕向往,或难以置信,或幻想不已,或嗤之以鼻。我甚至以为,以至于到了今天,科技昌明的年代,我们历史、考古学家并没有将上古时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清楚,很多地方迎合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之说,其中有一些令人沮丧的成分。欢至午夜,众人酒散,恍惚之中,行走在泾川城中,微风细腻而清凉,令我想起几年前攀登崆峒山的情境,那也正值春天,草木复苏,只是大地和空气比较干燥,在崆峒山上,想起黄帝问道广成子之事,确乎神异,但充满了高维智慧,如广成子所言,“至道之精,杳杳冥冥。无视无听,抱神以静。必净必清,无劳而形。慎内闭外,多知为败,与日月参光,与天地为常”。等等,也很切中当下人群。
至宾馆开窗,躺下,风吹杨树叶子的声响似乎古老的乐器,传达着一种静谧之中的隐秘信息。我想到,对于过往的历史和消失了的事物,尤其是时间之中人的真实行迹和行为,后人的发现和研究似乎都是徒劳的,发掘与考古发现的那些,只可能是凤毛麟角,甚至还会大相径庭。我始终觉得,时间这个无形的容器之中,肯定隐藏了诸多秘密,其本质就是拒绝透露与解释,因为,天地之间有些事物的本质,其本质就是不可“道于外人知”。对于不断衍生与消亡的人类世界,时间就是最大、最有力量的“神”。
早上的泾川,清风到处,徐徐之间,百草摇曳。中午暴热之时,随当地几位朋友去西王母宫。据说,西王母本姓杨,名回,为一女性氏族首领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说,“西海之南,流沙之滨,赤水之后,黑水之前,有大山,有曰昆仑之丘。有神人面虎身,有文有尾,皆白处之。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,其外有炎火之山,投物辄然。有人,戴胜虎齿,有豹尾,穴处,名曰西王母。此山万物尽有”。作者不详的《汉武内传》则说,“视之年可30许,修短得中,天姿掩蔼,容颜绝世,真灵人也”。这两种说法,很多人当然相信后者,也认同所谓的“西王母”,乃是一部落首领,而非《山海经》中之神异荒诞。而我则更认同《山海经》说法,也觉得,人类的能力大致是由高到低,或者干脆说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。以此来看,整个《山海经》都应当是上古年代的一部地理志,它所包含和记载的范围,也不仅仅只是东方,很可能是当时整个人类世界的一部方志。
回山之上,王母宫巍然,仙气飘飘,其中不仅供奉西王母、东王公(也叫扶桑大帝、东皇公,与西王母相对,全真教祖师),还供奉中华民族人人耳熟能详的三皇五帝(燧人、伏羲、神农,黄帝,颛顼、帝喾,唐尧、虞舜),西王母的形象雍容大方,宽脸长眉,神情慈祥,其他神祇也都按照道教之记载,进行塑像。在其中瞻仰,我觉得还是应当俯身低首,不论这些人物是神仙还是凡民,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,即便有荒诞之记载,可也都是在东方大地生存过的,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生产、生活乃至文化、精神发展都有着强大推动力的功德先辈。
日光愈发炽烈,高原是距离天空和日月最近的地方,地势越高,人越灵性,与万物的关系更加亲密。瑶池、浴苑、石窟等等,都与西王母有关,泾川人以为,西王母真的是自己的先民先祖,而不在“昆仑之丘”。这种朴素的认同感,反映到现实,就是不断以西王母的名义进行命名,甚至开凿石窟。人对于美好之人的崇尚,是天性,民俗学家也认为,西王母乃至中华民族“美神”的化身,她不仅具有异乎寻常的“神力”,也是中华民族妇女之美的“典范”与“标杆”。徜徉浏览之间,面对消失而又复原、再造了的古人形象,不由得心生敬意与爱意。人生于世,芸芸众生,在浩茫的时间之中,有几人能被后人记住与感念,而中国人所有的伟大梦想,无非“死而不亡者寿”,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“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而身存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“修身治国平家治天下”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如泾川这等秦陇交汇之地,建有规模宏大的寺庙,完全不足为奇,而称奇的则大云寺博物馆存放的14粒舍利。这些舍利,得益于隋文帝杨坚,其年届60岁时候,特别下诏在全国各地供奉佛舍利,大云寺便是其中之一。清人严可均编纂的《全隋文·先唐文》收录了杨坚的《再立舍利塔诏》,全文说:“朕祗受肇命,抚育生民,遵奉圣教,重兴像法。而如来大慈,覆护群品,感见舍利,开导含生。朕已分布远近,皆起灵搭,其间诸州,犹有未遍。今更请大德,奉送舍利,各往诸州,依前造塔。所请之僧,必须德行可表,善解法相,使能宣扬佛教,感悟愚迷。宜集诸寺三纲,详共推择,录以奏闻,当与一切苍生,同斯福业。”
杨坚“天性沉猜”,但对于中国历史,却是厥功至伟,在诸多的评价之中,其后世皇帝朱元璋说,“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,赏功弗吝,节用安民,时称奔驰。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。”我以为是恰切的,妥当的,只是,在胜王败寇的历史语境当中,隋朝国祚太短,而被后人屡屡忽视,其父子恶名大于功名。与当地诗人雨歌等入地宫参观,在佛舍利面前,我惊讶、肃然,看到那些五颜六色、质地坚硬,甚至在2000吨重压下都不会粉碎与变形的高僧遗物时候,有些恍兮惚兮的缥缈感,人之肉身,软硬组合,而高僧何以体内有此结晶物呢?这个问题非科学方式可以解答,似乎是大虚无之后的大实在,大境界之中的大见证。在这个世界上,总有一些人心怀大愿,志趣高渺,不为凡俗所知。
站在大云寺高塔之下,日光直射,有一种杀伐的感觉。四周黄土高冈,植被丰然,似乎也感觉不到荒芜,因为,有信仰的地方,精神已经百草丰茂,日月朗照了。
乘车再到罗汉洞乡罗汉洞村,村子背后的一道绵长石崖之上,绵延着一道石窟,其中佛龛众多,一旁俨然有烟熏的黑迹,大致是凿窟者日常烟火饮食所致。罗汉洞长约5华里,在泾河北岸,天地山冈之上,俨然是一种神迹。我们几个站在护栏外仰望半晌,隐约可见诸多的佛像,在山窟之中安详。我想到,泾川之地,俨然是一个宗教流播深厚之地,不然,何来如此之多的寺庙与石窟,而且横竖皆成大规模大境界。西王母、东王公、三皇五帝,乃至与西来的佛陀共处一地,各在各处,各自氤氲缭绕与安然醒目,从另一方面,证实了泾川之地的兼容性,而这种兼容性,一方面来自民族之间的混血和融合,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信仰之间的兼容并蓄与和谐同在。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,“(泾川)在(平凉)府西南。周宣王时,猃狁内侵,至于泾阳。谓此地也。汉置县,属安定郡(治所在今宁夏固原)。”这也说明,泾川之地,想来是一个文化的、交通的、民族的和宗教的通道,它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必须始终保持一种接纳的勇气和更新的活力,才能在蛮长时间之中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中,不断生衍发展,保持无可断绝的生命力。
当地朋友说,上世纪七零年代,在泾明乡白家村东庄社的牛角沟,出土了距今3-5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,以及多个砍伐器、刮削器及动物化石等,1984年2月《人类学报》第三卷第1期刊刘玉林、黄慰文、林一璞《甘肃径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》一文中说,“发现的标本为一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,出土时已裂开多块。它包括右额骨鳞部一小片、右顶骨的大部、较完整的右颞骨、枕骨的大部和左顶骨的一小部。标本呈淡褐色,有一定程度的石化。……甘肃平凉的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。它在人类进化系统处于早期智人的地位。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。”
我在照片前伫立许久,盯着那一枚白色的头盖骨,想象5万年之前,在泾川生活的这位年轻女性,这头盖骨之下,该是怎么样的一张面孔?她的父母是谁,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以及近亲?死亡的时候,她有无结婚,是不是有自己的后代?又是怎样的灾难,突如其来的还是自然而然、不可抗的?凡此种种,今人无法想象,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这是一个人,一个女人,一个女儿、妻子、妹妹,在今人难以猜想的远古时期,如她这样的人们,究竟遵循了怎么样的生存态度和法则?那时候的世界和人类,是不是真的互通有无,往行无极,甚至辽阔无际?真的源自同一个母亲和族群呢?
这是泾川的纵深,也是人类的纵深。未解之谜遍布自然界,后人的猜想总是牵强、以偏概全。深入牛角沟之中,多的是洋槐树和杨树,其中甘泉产自石岩之下,涔涔、汩汩,滴水不断,有着一种柔韧的力量。落日西行之际,我们坐在一户人家门前,吃到了浆水面,还有那种自制的凉粉。这两种甘肃民间美食,朴素而纯正,味道浓烈,令人喜欢,河水无声,古树之中,村庄坐落在牛角沟的密林茂草之中,这种情形,像极了我多年前的乡村生活,而泾川之地,也与巴蜀自然地貌颇有相似之处。由此我想到,大地从来都是相连共生、欣欣向荣的,《礼记·中庸》言说,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”,真乃至理。
与朋友话别之时,清风适时奔袭而来,又是一阵清爽。坐在高铁上,想起李商隐在泾川的时光,该是旖旎与美好的,但也得意与忧虑共生,他得遇良友,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旅程,又写下了诸多诗篇,但其专投“李党”,大致是受人诟病的,对令狐楚和令狐绹等人的背叛,李商隐的内心肯定也是很煎熬的。但李商隐在泾川的现实时光,当是其人生最美好的,随之而来的艰难,最大的打击该是其妻王晏媄病逝。李商隐两首最著名的诗歌,应当就是写给自己妻子的,第一首名曰《无题》,“昨夜星辰昨夜风,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隔座送钩春酒暖,分曹射覆蜡灯红。嗟余听鼓应官去,走马兰台类转蓬。”格调虽然转暗,但其开头却是欢快的,大致,李商隐一方面欢喜、满意自己与王晏媄的婚姻,又觉得自己如此之远,总有些漂泊寄居的惆怅挥之不去。
第二首便是《夜雨寄北》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有人认为,此诗并非李商隐写给其离世妻子,而是写给其某位好友的,但从整个诗歌的语境和口吻看,诗人“寄北”的这个人,当是与其关系亲密之人,我固执以为是其写给亡妻王晏媄的,这其中,反映的,就该是夫妻之情。
李商隐诗歌自成一家,清代诗人和史学家吴殳说,“于李、杜后,能别开生路,自成一家者,唯李义山一人。”另一个清代诗人叶燮也说,“(李商隐诗)寄托深而措辞婉,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。”
高铁纵驰,由甘肃而陕西,秦岭之中,横入巴蜀,夜色之中,想起泾川之行,人、物和感觉历历,入心入脑,尤其是西王母、舍利子、罗汉洞、大云寺、牛角沟古人类头盖骨,这些文明的存在,似乎也正是泾川人文精神的见证。同时也忽然觉得,在古人的身上及其行迹当中,总能够看到中国文人古来见天地、见众生的胸襟情怀与绵长情义,当然还有幽秘心曲与委婉象征,对于李商隐,除了他的那些闻名遐迩的佳作之外,我还喜欢他的《北青萝》一诗,“残阳西入崦,茅屋访孤僧。落叶人何在,寒云路几层。独敲初夜磬,闲倚一枝藤。世界微尘里,吾宁爱与憎”。尤其最后一句,令人默然,也倏然惊醒。
作者简介:
杨献平,河北沙河人。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。作品见于《天涯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刊。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、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、在场主义散文奖、四川文学奖等。主要作品有《沙漠里的细水微光》《黄沙与绿洲之间》《弱水流沙之地》《沙漠的巴丹吉林》《张骞的道路:从河西走廊到阿拉善》《黄沙飞雪:河西走廊之书》等边地散文系列,《生死故乡》《南太行纪事》《作为故乡的南太行》《南太行大地往事》《自然村列记》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,以及书写当下时代个人现实和精神困境的《中年纪》《世上最好的事情》及多部长、中和短篇小说,诗集《命中》等。现居成都。中国作协会员。
相关新闻
精彩推荐
版权与免责声明
1、凡注有“网行风”或“HUGO”的稿件,均为泾川网行风版权稿件,转载请注明来源为“泾川网行风”。
2、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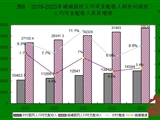


 [
[
 [
[